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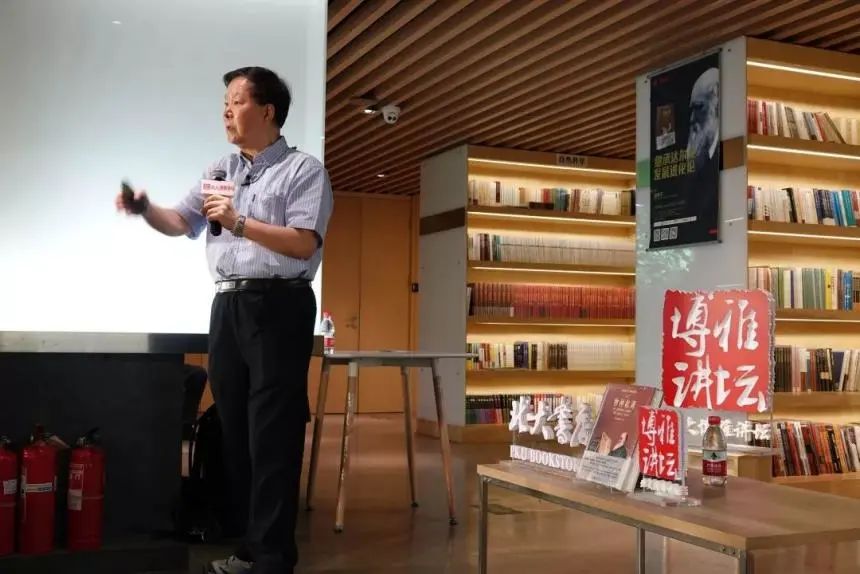
“無心插柳”做科普,舒德幹院士火了!
(神秘的地球uux.cn)據北京大學出版社: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獲得者、進化古生物學家、長江學者、西北大學博物館館長、76歲的“重量級寶藏UP主”……
當這些詞匯匯集在一起,一位和藹可親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舒德幹出現在大眾眼前。
有人說古生物學是“冷門學科”,他矢誌破解達爾文世紀“懸案”,在《自然》《科學》多次發文,發現的“天下第一魚”引發全球轟動。
有人說院士做科普是“大材小用”,掌握本領域最前沿知識的人,卻給公眾講解一些皮毛,但他的回答是“甘之如飴”“做好科普也並非易事”,他的科普視頻深受各個年齡段的觀眾喜愛。
有人說“雲南蟲是原始脊椎動物”,給學界和公眾造成了明顯的誤導,他多次發文,公開澄清,堅持科學研究需要求真務實。
“進化古生物學”研究的佼佼者
“板凳雖冷,心胸火熱,激情澎湃,科學發現的快感妙不可言。化石貌似死板冰冷,其背後的演化故事卻鮮活靈動。”
現任西北大學博物館館長的舒德幹,可謂是“進化古生物學”研究的佼佼者。
他曾經主持翻譯《物種起源》,並撰寫“導讀”和“進化論十大猜想”。他提出的“動物界三幕式爆發成型假說”,是唯一一個由中國學者提出的進化論十大猜想。在澄江動物群和寒武紀大爆發研究上,他形成係統性科學發現,其多項重要發現和理論假說,獲得學界廣泛認同,並被錄入多國教材、辭典、專著。
他也是我國早期生命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之一,其研究團隊在古生物學研究領域已進入全球第一梯隊。他們在《自然》《科學》上發表了十餘篇重要論文,發現了最古老最原始的脊椎動物“天下第一魚”昆明魚目,創建了古蟲動物門,首次發現了後口動物亞界譜係起源證據,並構建了地球上最早的動物樹框架,提供了遠祖們陸續創造“第一口”“第一鰓裂”“第一頭腦/第一脊椎/第一心髒”等基礎器官係統的可靠化石證據,在國際學術界引起轟動。
國家自然科學獎評獎委員會評價說,這些成果“是對達爾文進化論的重要發展,科學價值重大,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莫裏斯指出:“能夠對這兩個極富挑戰性的進化論題作出如此重大的貢獻,其意義不言而喻;而且,即使一個科學家隻對其中一個論題作出如此重要的貢獻,那麽,這位學者和他的祖國都將會因此而引以為豪。”
“進化論的十大猜想(假說)”
上世紀末期,舒德幹在澄江動物群研究中取得重大進展,在英國《自然》雜誌上連續發表4篇論文,尤其是1999年發現的“天下第一魚”,被學界公認為人類在脊椎動物大家庭裏的“鼻祖”,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
1999年元旦假期,舒德幹在從雲南采集的標本中發現了“天下第一魚”的魚化石。“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脊椎動物!”他將兩枚標本的其中一枚命名為“鳳姣昆明魚”,鳳姣是他母親的名字;另一枚命名為“海口魚”。
1999年11月4日,《自然》以長文形式發表了這一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重大突破性成果,將已知最古老脊椎動物起源向前推進了五千萬年!該雜誌以《逮住天下第一魚》為題的專題評論認為,“舒德幹等人發現的兩條魚——是學術界期盼已久的早寒武世脊椎動物,填補了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重要空缺”。國際學術界為之轟動。
英皇家學會院士道金斯在專著《人類祖先的故事》中提出,從原始單細胞生命演進到人類共經曆39“代”祖先,而昆明魚最接近第18代祖先。
“第一魚” 昆明魚目的化石及複原圖。它不僅具有可信的脊索構造、人字形肌節、肛後尾,更誕生了脊椎骨,頭腦眼。
舒德幹說自己近40年來一直在“沿著達爾文的足跡前行”,一步也不敢懈怠,終於在破解達爾文世紀懸案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在距今5.4億年的寒武紀初期,地球生命演化史上出現了一次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生命創新事件,即在不到地球曆史1%的“瞬間”,爆發式產生了90%以上的動物門類。節肢、腕足、蠕形、海綿、脊索動物,等等,一係列與現代動物形態基本相同的動物,在地球上來了個“集體亮相”,形成了多種門類動物同時存在的繁榮景象,俗稱“寒武紀大爆發”。
這一奇特現象至今仍是進化生物學的一大懸案,構成當代自然科學六大難題之一。達爾文在其著作《物種起源》中提到這一事實,並大感迷惑,他認為這一事實會被用作反對進化論的有力證據。
主張漸變論的達爾文堅持認為“自然界不存在飛躍”,大爆發不過是化石記錄保存不全造成的假象。然而,100多年後,化石記錄越來越多,“動物大爆發”景觀越來越清晰,美國科學院院士古爾德提出“一幕式爆發”猜想,使得許多人附和“幾乎所有的動物都站在同一起跑線”,這無疑令神創論者喜笑顏開。
而舒德幹的研究成果,卻有力駁斥了神創論。2008年,基於全球三大著名早期化石庫、尤其是澄江化石庫的真實記錄,舒德幹在著名英文雜誌《岡瓦納研究》發表長文,將寒武紀大爆發的本質內涵與地球動物樹起源及演化成型緊密聯係在一起,創新性提出“三幕式寒武紀大爆發”新假說,實證了三幕式爆發依次誕生了動物界的三個亞界,從而首次完成了早期完整動物樹框架的構建,破解了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的世紀疑惑。
“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清貧,頂得住壓力,‘十年磨一劍’曆來是我們團隊的傳統。磨劍很清苦,但鋒利的劍能破解重大學術難題。30年來,我們磨出了兩把‘長劍’和四把‘短劍’。‘長劍’一是澄江動物群,二是清江動物群。”舒德幹曾經在采訪中感慨道。
回望自己幾十年來的人生和事業,他對進化古生物學的熱愛溢於言表:“地史舞台上最美妙絕倫的大戲乃是40億年無奇不有的生命演進,變化莫測,令人歎為觀止;透視進化奧秘,令人陶醉,樂此不疲。借助嚴謹的科學實證以破解達爾文猜想和世紀難題,探索旅程的艱辛總能被發現真理的愉悅所蕩滌;人生的極致幸福,無出其右。”
“被逼出來做科普”的寶藏up主
“我曾經在科學研究上做過一些工作,如今年齡大了,更感到最重要的事是要讓‘學術基因’得以傳承,建立一個能夠可持續發展的學術梯隊。具體到科普工作上,我想要為各種優秀科普作品的問世鳴鑼開道。”
在科學研究取得重大成就之後,舒德幹“被逼出來做科普”——許多研究單位和大眾媒體“逮住他不放”,日本“生命之海”博物館聘任他為榮譽館長,要求他每年作不同主題的科普報告。
他於是開始將“高冷的”古生物學,用“接地氣”的方式給大眾進行科普介紹,收獲了諸多關注和眾多好評。
盡管科普工作起初是“被逼的”,但舒德幹很快由被動轉為主動和自覺,他用“甘之如飴”形容自己做科普的狀態。即使科研任務繁重,他依然擠出時間做科普,科研和科普在他看來理應“雙翼齊飛”。
他認為,科普的意義不僅在於傳播了進化古生物學的諸多重要新發現,而且與大眾分享了中國學者的科學思想,這是一件既利於社會發展和科學進步,又令大眾愉悅的美事。
為了能夠深入淺出地講解古生物學知識,解釋生物進化的複雜過程,舒德幹在PPT中精心製作各種直觀的圖片,使深刻的理論淺顯易懂。
他的科普視頻,有麵向普通觀眾的幾分鍾短視頻,有幾十分鍾的中視頻,還有通過大學和研究所平台發布的長視頻,知識基礎不同的觀眾可以“各取所需”。在一次給小學生作報告後,一位九歲的小朋友告訴舒德幹:“我聽懂了80%。”
在學術上是前輩、在年齡上是長輩的舒德幹,總習慣在自己科普視頻的結尾說一句“請大家批評指正”。他在中視頻和長視頻中設置了與觀眾的互動環節,通過彈幕觀察觀眾們的反應,和觀眾平等交流。
“留言裏不乏一些真知灼見,有鼓勵也有善意的批評,還有網友會調侃我的‘湖北腔普通話’,很好玩。這種及時的互動,是網絡科普的一大優勢。”
在科普事業中,他一直主張做“高級科普”,即富有思想創新的科普。
在話題選擇上,他既注重介紹有趣的古老生命跌宕起伏的演化故事,也會介紹達爾文、牛頓、孟德爾等偉大科學家如何實現科學思想創新的生動故事,注意引導青少年關注學術思想創新。
“三幕式寒武紀大爆發假說”也是他科普的重要內容,這是“進化論十大猜想”中唯一由中國學者提出的科學猜想或假說,他認為自己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舒德幹強調,“愛青年人,要從骨子裏愛,關愛他的學術前途,給他們創造條件,留足夠的發展空間,讓他們能嚐到做學問的甜頭和發現的快樂,力爭讓科學文化基因代代傳承。”
通過科普視頻,舒德幹對年輕觀眾有兩點期盼。
一方麵想讓他們在聽故事的過程中獲取一些進化古生物學的有趣知識,更重要的是啟發青年人不光是輕鬆愉悅地“看熱鬧”,還要學會“看懂科學的門道”,培養他們動腦子的好習慣。最好通過思考,青年人自己能夠在實踐中創造新知識、創造新思想。
另一方麵,他期盼年輕觀眾能夠培養出“理性質疑”精神。我國傳統文化非常優秀,但也存在一些消極因素,包括“大人說話小孩聽”“老師傳授知識,學生被動接受”“分數為王”等傳統現象,這實際上成為了我國科技創新的無形障礙。因此,他在科普過程中特別鼓勵青年聽眾能夠學術平等,勇敢質疑,理性質疑。
“不怕得罪人”的耿直院士
“我和團隊的青年人一直嚴格要求自己,希望能夠堅持科學精神,堅守科研誠信原則,勇於堅持真理,敢於擔當,敢於同違反科研誠信的行為說‘不’。”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舒德幹主張院士專家們都應該自覺地為科學研究和科普工作蓬勃開展營造良好氛圍;並提出,他們的責任還應該包括,在學術上與年輕人平等對話,推動百家爭鳴,自由探索,服從真理;年長者尤其要注意向青年人的創新精神學習。同時,也應該直麵科研和科普中的各種誠信問題,敢於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人。
科學精神的靈魂是理性質疑和批判。科學工作者要敢於質疑,經得起質疑,如此方能創新。
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的“雲南蟲是否原始脊椎動物”事件中,舒德幹就是那個秉持科學真理,堅持科學精神的耿直院士。
事件起源於7月8日,我國幾個學者在美國著名雜誌《科學》(Science)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文章得出了一個頗為轟動的結論:長期存在爭議的雲南蟲,是原始的脊椎動物。
這一結論,顛覆了常人對人類所屬的脊椎動物大家庭的認知,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大量報道,但同時也引來了科學界的爭議。
雲南蟲化石圖及複原圖,它沒有可信的脊索構造,沒有人字形肌節,沒有肛後尾,沒有脊椎,更沒有頭腦眼。
其實,如何正確看待 “疑難動物” 雲南蟲的生物學地位,在上世紀末曾經一度是學術界的一個棘手難題。
1990年代,一個中美合作研究小組起初認為,雲南蟲是低等脊索動物,後來又將它升格為脊椎動物或 “有頭類”。2003年春,舒德幹團隊在《科學》雜誌撰文,報道了雲南蟲類的一個新種,並對西北大學采集的數千枚雲南蟲類標本進行了全麵考察,確證它們既不具備低等脊索動物的脊索、肌節和肛後尾,更沒有脊椎動物專有的頭腦眼和脊椎骨的跡象。基此,他們全方位分析了雲南蟲類的生物學地位,認為它應該是後口動物亞界中的原始類群,與低等脊索動物和高等脊索動物(即脊椎動物)皆無關,而與非脊索動物的半索動物門和古蟲動物門相近。
此後,雲南蟲類的 “脊椎動物說” 很快被學界摒棄。
舒德幹將雲南蟲稱為“與我有30年交情的‘老朋友’”,憑著過去30年來對澄江動物群中的 “疑難化石” 雲南蟲的研究,看到它再次被 “升級為” 地球上 “最高等” 動物類群脊椎動物,舒德幹大感震撼。尤其是文章麵世後,被國內各大媒體作為“重大發現”炒得沸沸揚揚,已經給學界和公眾造成了明顯的誤導。
本著為科學發聲正名的初衷,7月25日,舒德幹在《知識分子》發布文章《爭鳴 | 舒德幹:被熱炒的雲南蟲,究竟是不是脊椎動物?》,提出質疑。
他指出,盡管該文章發表在美國的《科學》上,但它在科學邏輯、證據和結論上都存在顯而易見的問題,雲南蟲離脊椎動物相去甚遠。雲南蟲不具備脊椎動物大家庭成員必備的脊索、肌節、脊椎骨、肛後尾和頭腦眼等基礎器官,它在進化道路上與“第一魚”昆明魚目早早地就分道揚鑣,成為“兩股道上的車”,並步入了死胡同。
雲南蟲隻是 “蟲”,屬於 “無脊椎動物”;昆明魚目是 “魚”,這些 “天下第一魚” 屬於真正的 “原始脊椎動物”。作為無脊椎動物的雲南蟲,與作為脊椎動物始祖的昆明魚比較,兩者相隔巨大鴻溝,不可混為一談。
然而,7月28日,該論文的聯合通訊作者、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薑寶玉教授很快就在《知識分子》上發布《爭鳴 | 論文作者回應:雲南蟲具脊椎動物特有特征》一文,針對舒德幹的質疑做出回應,堅持將雲南蟲視作脊椎動物。
兩篇“爭鳴”文章發表後,不少人支持舒德幹並建議:“關於雲南蟲地位確定的是非曲直已經十分清楚了,您不必再花費筆墨補充證據了。”也有非專業人士提出,“現在的問題是,公眾並不清楚,判斷是否脊椎動物的標準究竟是什麽?”希望能得到明確的解答。
舒德幹對此再次做出回應。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進化古生物學研究的科學工作者,他表明自己有責任也有必要借助大眾媒體,對論文中的錯誤結論做出澄清,以正視聽,否則會以訛傳訛。並再次強調自己指出的是該論文的諸多“錯誤”,而不是“不同觀點”。
舒德幹坦言,自己之所以如此較真,是因為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它既是一個科學的真偽問題,同時還涉及一個人人關心的人文哲學命題:究竟誰才是人類真正的遠古祖先?誰為祖先們創造了眾多基礎器官?科學研究和科學傳播上都不能稀裏糊塗;我們人類不應該隨意接受一個強加給自己的“四不像”祖先!
他也堅信,科學是一項神聖的事業,需要有嚴謹的科學方法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希望科學界能從這個事件中引以為戒。
(责任编辑:郭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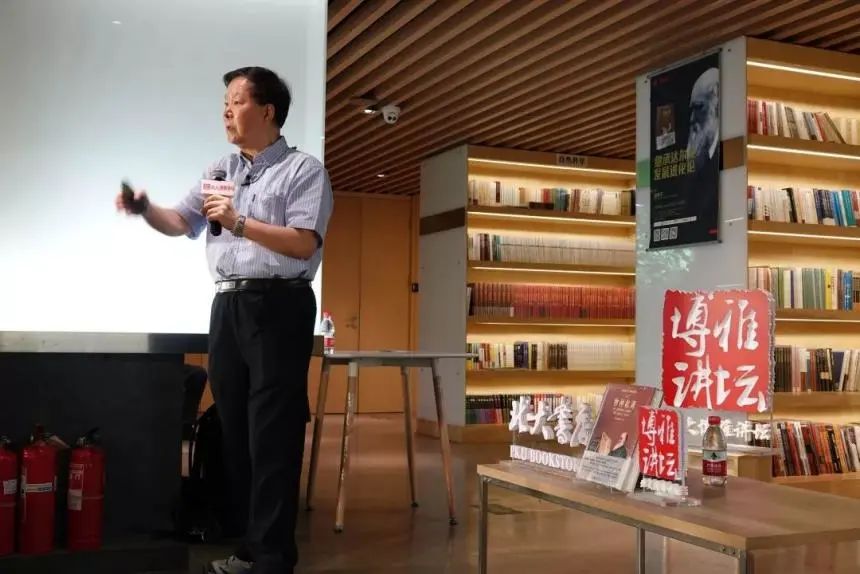
 自信開放,彰顯雍容大度、開放包容的中國氣度。...[详细]
自信開放,彰顯雍容大度、開放包容的中國氣度。...[详细] 由於業績公布時間在收盤後,受業績影響的股價變動主要發生在本周。...[详细]
由於業績公布時間在收盤後,受業績影響的股價變動主要發生在本周。...[详细] 40年前離開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裏早早擠滿了送行的鄉親,大家一聲不響等他起床。...[详细]
40年前離開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裏早早擠滿了送行的鄉親,大家一聲不響等他起床。...[详细] 河北張家口市打造冰雪裝備製造業基地,冰雪產業鏈條不斷延伸冰雪市場前景廣闊,大有可為。...[详细]
河北張家口市打造冰雪裝備製造業基地,冰雪產業鏈條不斷延伸冰雪市場前景廣闊,大有可為。...[详细] 一方麵,哈爾濱擁有得天獨厚的冰雪資源,其冰雪旅遊在國內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吸引了大量遊客前來體驗。...[详细]
一方麵,哈爾濱擁有得天獨厚的冰雪資源,其冰雪旅遊在國內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吸引了大量遊客前來體驗。...[详细] 四個切口也是四個突破口如何理解一個抓手,四個切口?劉鶴指出,一個抓手就是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統一。...[详细]
四個切口也是四個突破口如何理解一個抓手,四個切口?劉鶴指出,一個抓手就是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統一。...[详细] 4月8日,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详细]
4月8日,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详细] 弘揚冬奧精神胸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而上、追求卓越、共創未來講話中,習近平指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廣大參與者珍惜偉大時代賦予的機遇,在冬奧申辦、籌辦、舉辦的過程中,共同創造了胸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详细]
弘揚冬奧精神胸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而上、追求卓越、共創未來講話中,習近平指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廣大參與者珍惜偉大時代賦予的機遇,在冬奧申辦、籌辦、舉辦的過程中,共同創造了胸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详细] 看老鄉的糠團子差很多,習近平主動換著吃。...[详细]
看老鄉的糠團子差很多,習近平主動換著吃。...[详细] 內蒙古通遼地區、赤峰地區、農安地區水分15%新玉米貿易商收購價格,均較前一日上漲40元/噸。...[详细]
內蒙古通遼地區、赤峰地區、農安地區水分15%新玉米貿易商收購價格,均較前一日上漲40元/噸。...[详细]